
偏安东南一隅的厦门,正呈现出她刚好的姿态,当地设计在国内外设计圈内发出了越来越多的声音。城市腹地小所带来的亲密距离感不仅体现在交通上,更体现在彼此的合作上,时不时会有跨界合作推出,形态自由且配合高效。在今年3月份的设计上海之前,我们和古奇前往厦门拜访了汤建松建筑工作室,以原木材质为主的空间干净,大胆留白,沙、石、绿植点缀其间,有着东方人安静清透的处世之美。


这是汤建松自己设计的办公室。2007年,汤建松成立汤建松建筑空间,期间多次获得亚太地区等国际设计金奖。他将自己定义为一个建筑改造师,并不涉猎新建筑领域。在汤建松看来,中国不需要太多新建筑,在中国急需的是建筑改造,近30年内中国产生了大量的不管是结构还是功能上的建筑次品,建筑的合理性被埋没,中国的建筑师应该更理性去看待这些新的旧建筑。推倒重建不见得是最好的办法,更有效的因地制宜,让旧建筑重生,是这个时代建筑师的价值所在,并由此开展自己的建筑实践。

去年年底,汤建松与王琦、杨鹿童三人组成退化建筑研究室,尝试将建筑与不同媒介对接,用建筑思维和艺术生产的方式输出城市和建筑观点,同时保持开放形态。他们推出了许多极具趣味且有建筑意识启发的项目。“城中村负模”取自厦门城中村村民自建建筑之间所能看到的天空切片,将这些灰度切片附加各种鲜亮颜色,高密度挤压、低廉出租、只能开30度的窗户、无人接管的街道死角,这些城中村的日常被重色所放大,从中可以看见城市化过程中所催生的特殊尺度景观。“城市尺度”项目则用三个“1”的方式将日常我们所忽视的尺度1米、1平方、1立方强化重现,拉回对建筑基本构成最初的认识。
“世界太左的时候你右一点,太右的时候你要左一点,退化也是一样,现在进的东西太多了,便退一点”。这是退化的态度,不妨都退一点看看,捡回日常认知。
/ 梵几 x 汤建松 /

朱晗:设计过那么多空间作品,如何总结自己的设计风格和审美倾向?
汤建松:如果一定要总结设计风格的话,这有阶段性,今年是这样,明年可能有变化,但会有一个相关联的主线。我认为形式没那么重要,要做成什么样子不重要。也希望自己没有审美上的约定和束缚——比如这个东西是好看的,这个东西是丑的。有些东西稍微理智一点它确实是丑的,但稍微感性一点又没那么丑。这个受我太太影响,她一直说我审美上有偏见,其实想想是有一点偏见的。每个人都有自己对光、对美、对事物的常识。
朱晗:你所说的常识指的是什么?
汤建松:常识就是回到人的最根本,每个人认为舒适的部分。你自身认为合理的部分就是常识,而不是外界他人告诉你这个是好与不好。一个人的常识是发自内心的,每个人的常识都会有一些不一样,这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差异性。



朱晗:个人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建筑师或者是设计师?
汤建松:雷姆·库哈斯。他的建筑不是一个单体上的建筑。我们可能觉得CCTV大楼特别丑,但其实这是一个表象,为什么做这个建筑本身比做这个建筑本身还重要。你认为这个建筑本身是什么样的,开始自己认知建筑的系统,或者是认知城市的系统,我觉得这个其实比房子本身重要得多。作为一个建筑师,只要有好一点的审美,就可以造出一个好看的房子,这个难度不高。但是你为什么想造这个房子,其实大部分人都讲不出来,那些功能性的需求涉及到的只是房子本身而已。




朱晗:简单介绍下你们最新成立的退化建筑研究室。
汤建松:退化建筑是以研究为主的工作室。基本上目前还是偏实验性的工作室,所以自由度会很大。我们希望以后就是一个超高自由度的工作室,现在也没有100%实现,因为做项目其实会碰到很多的外力问题,但还是能控制这个节奏的。接下来我们基础立足点还是在厦门这个城市本身,小城市的劣势在于有一些公司类型的合作很不成熟,所以做公司是比较痛苦的,作为工作室反而就也会轻松一点,因为可以有不同优秀的小团队在合作。
古奇:在选择项目的时候也会比较挑选。
汤建松:对,我们有特别普通的项目,也有财团性质的公司客户。但现在方向特别清晰,我们不把建筑变得特别高深,而要变得特别地简单直接。普通年轻人,能非常清晰地了解这件事情,而且会特别感兴趣。这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转变。因为建筑本身其实是建筑群或者是专业人士的领域内特别闭塞的东西,但在更早之前,或中国古代也好,建筑是特别平民的,普通人也是有参与的。现在我们花钱去买房子就得了,房子怎么建起来的,管道怎么布设其实跟我们普通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也不需要了解,我们现在重新去思考这个问题,让大家能去了解建筑。
古奇:三个人都有不同的其他工作,日常如何一起创作?
汤建松:我主要负责建筑设计,王琦之前做过杂志,杨鹿童主要负责视觉部分。为什么做这个事情,会先像做研究那样整理出来,前因后果写得相对完整,每个项目都会有相应的关键词。研究部分就纯粹的问题,剩下的就是我们项目的成果。从前到后全部梳理完,这个项目就结束了。大多退化的项目都用这个逻辑来做,会更彻底,每个项目都有来源跟完整的逻辑。


古奇:目前具体做过什么项目?
汤建松:城市测量City Size"1"是我们第一期的研究项目,我们从最基本的尺度开始,用金色的生日气球、“欢迎光临”红色地毯、粉色海绵呈现1米、1平方与1立方。一个立方的粉色海绵到设计部的时候,我以为设计师定错了,非常震撼的大。我们也把很多商店在用的“欢迎光临”地毯随机地裁成一个平方,在厦门六个区交界处的路口各放一块“欢迎光临”,用航拍的方式告诉大家这个是一个平方。我们做这个项目的目的是,让人感受到你周围的真实的尺度和城市的距离。很多高楼大厦实际上尺度比例已经超出了人认知的范围。这个退化就是把人认知的尺度往回拉,让你感受到这个尺度的存在。这样再一步一步地往下做,大家就了解我们周围的东西为什么会出来在这里?现在很多大众已经失去了对建造物或者产品的理解,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大家对周围事物能有比较直接的反应。我觉得这特别重要,很多年轻人现在对周遭事物的认识其实都比较模糊。
朱晗:工作室的形态更加自由,可以支持这样有趣的项目。
汤建松:对,我们做工作室有一个意义,要把公司在两年左右回到工作室。目前有一个团队跟我们合作。我们把主要的深化工作给他们,我们就可以有条件回到工作室。如果能达到,自由度会更大,可以选择性更自由的项目。很多项目挺好,但作为公司运行,理智告诉你这个项目不能接,接了可能就亏本了,但作为工作室相对无所谓了,就必须要接这种项目,我们退回来接自己认为适合的项目。
古奇:这是比较能坚持下去的一种方法,不会过度消耗。
汤建松:不会过度去消耗管理上的精力,要管理一个大型的设计团队,然后发现设计时间越来越少。我原本一个礼拜可能可以花3天,现在只能花2天甚至1天做设计,剩下的时间都去做管理。但我们必须要经历这种公司的规模管理,才能退回去。现在规模已经降下来的,但是还会逐步再降。做室内设计本身,做建筑改造也好,实际上是都算是耗资的项目,都需要特别严谨的团队去操作,当你有很好的外协公司的时候,你可以慢慢去做你最关键的那部分事情。



古奇:我非常理解你的想法,这也是我面对的问题,做一个经营者还是一个设计师。我现在在经营管理上投入的精力也特别大。因为一旦经营管理了之后,很多东西代替不了,职业经理人可以管理一个大众化的公司,但可能比较难管理一个在处处都要有点文化的公司。我目睹了一些前辈都很难坚持做设计,这也是我现在在想的一件事。
汤建松:做设计公司会好一点,因为毕竟跟做品牌是完全不一样的,品牌还是需要这些东西。不同的阶段你就会不同的思考,然后就做出不同的对应。我认为一个好的品牌,是一个不断在变化的品牌。如果不变化的时候,这个品牌就基本上消亡了,它存在的意义就是盈利,某种意义上已经消亡了。如果一直不断在变化,可能变得更老或者怎么样,但还在不断的延续。所以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品牌一定是根据创始人本身的思考做出相对应的调整的。


古奇:是,我们在努力做的就是别把自己的事做到无趣。
汤建松:同样花5年的时间,不同的人就会做不同的东西,做得比较好的设计师有一点是可以不断地在调整自己。所谓的调整甚至有一部分是否认自己,然后有一部分是调整自己,不怕重新开始的疯狂迭代,而且非常有效率。如果是一直不断贯穿自己的过去,或者是贯穿认为比较好的部分,这个设计师的进步就会特别缓慢,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就越来越远了。其实很多日本的设计师做得特别好,但是再过几年以后你会发现还是那样子的,因为他是内化的,设计的东西会变得特别无趣。
古奇:中国5年可能顶上日本10年、20年。这跟民族性有关系。中国包括欧洲的包容性特别大,日本是单一民族性属性,能坚持也有另外一个原因,日本人的性格包括整体经济状态,但中国完全是另一个环境。



汤建松:所以我觉得这个时期的中国特别有意思。
朱晗:包括很多的外来品牌也会给大家刺激。
汤建松:对,其实是这样的,在中国五年是一个非常大的时期,可以决定这个品牌在这个时代的生命力。五年,不作出对应的就直接被淘汰了,你可以守着自己,但是意义不大。我们现在特别担心我们的工作室成了那种正儿八经的事务所。我一直在做这个风格也会很轻松,我就培养一个团队,就跟流水线似的,就每年好像就生产这样的。但如果哪一天成为那种太正儿八经的事务所就差不多完蛋了。
古奇:如果我们三四十年后串门就更有意思了。
汤建松:是,那就更不一样了,现在大家其实都已经在开叉走自己的路。中国这个时期还是蛮好玩的。一个特别混乱的时期,特别有意思,有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情,没有那么高度地统一了,所以我觉得中国经历,不同的城市辨识度会越来越差,但这种高度统一的城市化,也会带来另外一个东西,就是一定要变,一定要开始分化,然后有开始大量地建筑,让每个人改变自己的东西,把这个套路全部打乱,以后这个城市的人都会变得不一样。




PROFILE
汤建松:生于1981年。现居中国厦门。2007年在厦门创立“汤建松建筑空间”,2016年,与王琦、杨鹿童创立“退化建筑”,汤建松多年来以小型建筑改造、空间设计作为主要工作方向。他认为近30年内中国产生了大量的不管是结构还是功能上的建筑次品,建筑的合理性被忽视,因此应更加理性地对待中国“新的旧建筑”,将对新建筑的过分热情逐渐转移到建筑改造中去。
/
采访:古奇、朱晗
图:惟简摄影
文字整理:舒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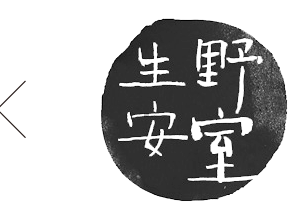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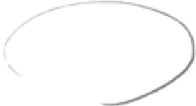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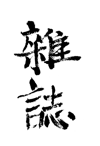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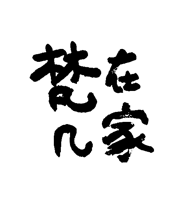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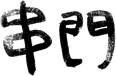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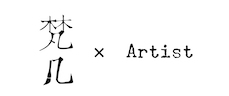

 客服部 service@fnji.com
客服部 service@fnj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