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品牌「不惑」的工作室位于钱塘江畔的一栋老别墅里,开阔的空间,独立的院子,幽静而自在。两位创始人汪浩和裘航将一层设为展厅和茶室,二层则是设计或打理日常事务的办公空间,创作、陈列、与友人共享一席茶,是他们在这里的生活。


关于器物,「不惑」有自己的坚持和理解。展厅里陈列的生活器物跨越地域和年代,有「不惑」自己的陶瓷产品,也有其他诸如玻璃、金属、木器作品,从中国的宋代、明代到日本的江户、明治时期的作品,也有当代的新的作品,“我们喜欢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器物,”汪浩说,“它们汇集于此,有一种融合的意义。”所以,努力探求传统文化于当代设计的传承进化,传达生活美学的意义,也是「不惑」一直坚持的事情。他们在自己介绍展厅的一篇文章里,引用了一段话:“符合生活美学的重要特质,就是要具备能跨越时间的美感,无论放在过去或者未来……富有经历感的物件,是长期使用而有岁月痕迹的物品,因为它们留住了生活的味道,以及人、事件和时间所赋予的意义,得以构建处恒久动人的生活美感。”两位设计师说:“我们追求的是一种人文的精神和学习的过程,去做现代人实用的东西。”「不惑」将远离华而不实与粗制滥造,一件不实用的日常器物不会长久的陪伴你,因为那些都违背了“用”的原则。
因此,两位给「不惑」展厅取名“元白”,元是开始之意,白则解释为“穿越时空的那道光”。穿越时空的那道光,将过去和现在的美好物件联结起来,「不惑」在这里,造务实良美之器,与世人分享。



梵几 X 「不惑」
朱晗:「不惑」品牌的名字来自孔子说的“智者不惑”,为什么想用这两个字作为品牌的名字?
汪浩: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觉得有一股欲望特别想去学。这是一个真事儿。我上学时的专业是工业设计和陶瓷,在当时是特别小的一个系,也是第一届,但从那时候开始通过一些课程,我开始了解陶瓷,之后因为自己喜欢,也会淘一点陶瓷品。 你知道这几年有很多日式风格的东西冒出来,好像说到陶瓷品,整个矛头都指向了日式风格。要想知道别人为什么那么好,作为设计师,不是仅仅买了喜欢的东西,之后的事情就不管了,而是要学习。大陆的陶艺工作室大概落后台湾三十多年,台湾又落后日本三十多年时间,这样累计起来就是六、七十年,但从做陶艺来讲,追根溯源,日本是从我们这里学过去的,但为什么他们可以保留的这么好,一直发展至今,我们却不行,是不是我们的能力就真的这么差?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想要真正自己动手去试试看,不死心,想去玩一下。
在「不惑」品牌发展的这一年多的时间之前,我们已经默默研究了近三年的时间,那时候只是投入,却越玩越上瘾,因为每一次都感觉做出的东西离自己想象的目标越来越近。现在回过头再去看,包括看「不惑」新出的一系列产品,我得出的结论就是:我们其实并没有落后那么多年。比如我们最新的产品,如果这不是我画的图,只是从这件产品的材质、份量和感觉来看,你告诉我是日本的东西,我一点也不怀疑,而且我还要说,它比日本的一些东西还要好用。于是我就在想,我们自己完全能做得到的事情,为什么就没有人去做呢?我觉得我们出的最大的问题是方向性的问题,还有就是相对别人来说,有一点懒惰。一旦取得了一点东西后,喜欢守着不放。日本就不同,传统的东西有,新的东西也有,既能交融,也能去碰撞,所以它在商业上呈现出来的,哪怕是零售,也让人觉得很丰富。不会像我们这样很偏执的只有这么一块那么一块的东西。


古奇:我觉得中国还有个问题就是因为方向太多,所以每一个方向都走不长。而且风气经常变换,今天也许流行日式风格,明天可能又变成另外一种,如果那样的话你会不会转变风格?
汪浩:我肯定是继续做。因为「不惑」一定不是去做日式风格的东西,只是去做现代人实用的东西。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刻意去强调什么是中国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词有点空洞了。中国分好几个阶段,古代、民国、现在都叫中国,我并没有刻意说要去做什么风格,只是自己在做自己的事情。只要我觉得能从别人那里学习到好的,我就会尽可能的把它学过来,自己用。我不喜欢「不惑」完全盯着产品,在设计的时候,外部的氛围对「不惑」的影响应该也是多方面的,这样她才能去选择、吸取。当你沉浸其中,就会发现陶瓷这个东西有太多是你不了解的:同样的材料、生产工艺,在不同的车间,不同的人手中,做出来的效果可能截然不同。很多不规律的东西是对我最大的吸引,之前我们有一种材质自然断档了,我们自己也很难再烧回去,「不惑」既不是工业化的生产,也不是完全标准的个人手工艺的凝结,我们追求的是一种人文的精神和学习的过程,所以「不惑」的意思其实就是「不迷惑」,希望她清清楚楚,能学的到。在取名的时候,大家都说这个名字会不会太常用了,或者别人会联想到其他的意思,我倒觉得没关系,从本质出发,做自己的事情,就不要去考虑别人说什么。等这个品牌做起来,她才能真正表达她要表达的东西。
古奇:你刚才说的,既不是工业设计,又非无意识的手工艺品,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
汪浩:对。我们还没有动手去做陶瓷的时候,我们对它大致的理解是用泥,简单地上一层釉,用不同的温度去烧制,蛮好玩的。实际上,日本在柳宗理这个时代已经解决了陶瓷品量产的问题,可以做到复制批量生产,但复制生产出现的问题就是产品特别僵硬,只能作为一种工具来使用,工具化的味道很浓。可是,人本身是去会挑选和鉴别的,人们虽然不懂技术,但是知道该怎么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好的产品一直可以流传使用,因为对于使用者来说,他并不知道这件物品是全手作的,还是借助设备来辅助制作的,他只能感觉这个东西我能越用越好,可以融到生活中去,而特别僵化的东西,自然而然就被使用者排除、淘汰掉了。所以这样一直流传使用的东西,是在设计这个领域里是真正为生活而设计的,更多地融入了人文和情趣在其中。现阶段在国内,我觉得人们很强烈的渴望这样的设计的存在,比如现在年轻人饮茶的习惯,对饮食的要求,明显能感觉到和我自己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


朱晗:目前,「不惑」品牌的产品大部分为茶器,是想以茶器作为开端,还是会专注于设计茶器?
汪浩:以后还没有完全定,当时选择茶器是因为自己喜欢,自己要用,就像做餐厅一样,首先是因为爱吃,先找一个兴趣,去满足自己的要求。我们选择茶器为入口,看起来简单,但给我们设计的空间并不大,难度却很大。比如壶嘴的角度,同样的形状,不同的材质,微小的差别就会影响到茶壶出水的感觉,使用的时候感觉是很明显的,做茶器其实是既不能放弃功能,也不能被功能所绑架。过去,我学工业设计时,理论上凡是同样造型、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东西,在功能上应该完全一样,但在陶瓷上就完全不一样,甚至在你泡几种不同的茶的时候,会明显的区别出来,不会有任何一个教科书上会告诉你壶嘴的角度应该怎样,所以你只能自己去尝试,摸索出合适的出水角度,找出哪个角度出水感觉最棒。像这样小的细节,可以把问题无限的放大。我们总感觉自己在做一件很小的事,但这个小的事其实对人的影响非常大,所以做茶器这个兴趣点会牢牢地抓住我。至于其他产品,我们先做茶器,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后再去做一些生活器皿,会有充分的沉淀,带着「不惑」的感觉去做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朱晗:现在用的两种材质:铁锈和青羊脂,铁锈需要用1300℃高温烧制而成,为什么偏爱这两种材质的质感和美感?
汪浩:其实“羊脂”是我们自己命的名字,来源于汝窑。汝窑分两块,一种是天青,跟羊脂比较更发蓝、发绿;另一种叫月白,就是我们所说的“羊脂”,材质是一样的,我们在做的时候把月白中油脂、光亮的东西抽离了,做了一些改进,瓷器上面的一层亮光部分被掉了,它就更加温润。做出来之后,羊脂给我们的感觉比较柔和,材质偏厚,所以在一些转折上就会比较圆滑,从而反过来影响我们的设计:特别圆润的东西用羊脂就很合适,比较尖锐的东西可能就不行。铁锈正好相反,和所有金属类的材质一样,偏薄,做一些型、转折、切面,它都能很好的体现出效果。铁锈和羊脂一刚一柔,所以两者结合最有节奏,看设计者如何把握,完全柔不行,太刚也不行。
古奇:制作中的折损率怎样?
汪浩:不惑的产品质量标准筛选下,成品率是比较低的。青釉容易出现黑斑和针眼,成功率在30%左右,金属釉成功率相对高些。所以最大的成本问题可能就出在折损上。


朱晗:在设计一件产品时,除了刚才所说的材质、美观度、耐用性和实用性,还会考虑其他什么因素?
汪浩:我觉得可能还要考虑一种感觉,是你在使用这个茶器时能够体会到,别人同样也能体会到的感觉。我们的新产品正式发布前会提前好几个月准备出来,这几个月中一定是自己先试用,因为用的时候就能发现很多问题,同时反思自己的初衷是什么,想要给别人带来的这样的感觉到底对不对。一般会有三种情况,一是这种感觉是对的,可行的;一种就是不对,和你的初衷不一样,是另外一种感觉,但这样也好;最差的一种要放弃的情况是:啥感觉也没有。对一件产品不再有感觉,肯定能说明某些地方出问题了。另外也能够在反复使用的过程中看看功能上到底有没有问题,有些效果我们可能也出于巧合得到的,但是巧合也是可以积累经验的,你就知道这个东西以后可能用在别的地方,就可以完美的解决这个功能的问题。
古奇:「不惑」的产品在比较传统一些的人群中、中老年的这些常喝茶的人中的接受度怎么样?
汪浩:我们不想把「不惑」做到这种层面的定论,我觉得和梵几的客户群差不多,对茶有了解,不是所谓的行业里的专家,但实际碰见行业里的专家我们也不怕。“传统”是一个综合性的词,这里面有褒有贬,传统里面肯定有好的东西,也有不好的地方,但如果你特意去坚持传统,可能就会停滞不前。日本有很多新的陶艺师,传统用的材质他也会用,但他给你的感觉就和传统是两码事,不完全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设计和传统没有什么可比性,我不指望我的东西能让每一个层面的人都觉得很好,这不现实。


古奇:我解读「不惑」的东西,在我的角度上看,和我设计家具的定位是一致的,我们吸取一些极简的东西,但是又融合传统,这就是我看到「不惑」的感觉。
汪浩:假设以后我再设计一款体量大的壶,用它喝英式茶,「不惑」一样也能做,那个时候那把壶可能就完全看不到日本风格的影子。就像我们买日本的东西一样,也有偏英式的壶,用来喝下午茶,那是生活上的事情。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共融的时代,共融的时代会产生一种情况就是什么都有,不像过去拜师学艺,只学一门手艺,但目前我觉得市场也好,传统手工艺也好,我的理解是不能特别死板,你得让它前进,跑起来,不管朝那个方向,这样它才能有支撑,才能做下去,如果按照原来的那套教条路数是走不下去的。
古奇:说到日本,我特别羡慕日本人的一点是,他们现在所谓的这种收敛和沉淀,当然也和时代有很大关系。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当中,每个人做一些事儿之后,就特别想扩大、连锁、占领市场、影响时代,但日本人却只是开一家店。我去年去Truck,就特别能够感觉到一个“停住”的状态:定期发布一点新品,预定一件家具要等七个月,节奏很慢。我去的时候碰巧看见老板正要出门去冲浪,那时候我想到自己,我工作的时候根本没有时间去玩。就是他这个能“停住”的状态让我回来反思很久,所以回国后,我就把一些计划停掉了,因为我发现我根本投入不了这么多时间把一件事做精做好。我们处在这个时代,整个潮流好像就让你没有办法停下来,做了一点这个,有一些成绩,又想做另外一部分。
汪浩:我觉得我们可能也需要一步步上来,因为我们已经在一个快车道上,如果你一个人慢,有可能被后面的人追尾,这个是很有可能的。也许我们可以适当地减减速,但如果是在日本这样一个比较内敛的地方,大家都是慢车道,都是自行车,你一个人骑个电瓶车快冲,你肯定也会惹祸。



古奇:比如当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东西时,最开始,你面对的世界特别大,积累在脑子里的东西特别多,这个时候释放出来其实很容易。但当你做一个东西时间久了,有了模式,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突破,在这么细微的东西中再创新,就是一个难度比较大的事儿,比如茶具,就这么点儿的东西,体量都固定了,线条也基本上有了风格,再怎么去突破?
汪浩:分几个方面来看。现在你们看到的杯子,大概有七八种,都是某段时间几乎是一口气做出来的,但是,之后又有很久不再做杯子了,就是刚才古奇说的,对杯子没感觉了,特怪。最近呢,我们对壶的感觉又特强,我就又去做壶去了。现在我基本上是有感觉的时候先做单品,至于成套的东西,我会看看产品自己相互是不是可以辅助一些。
古奇:「不惑」杯子的尺度是我用过的比较舒服的,传统的那种喝茶用的碗是特别小,很薄,白色的,喝功夫茶的。日本的杯比较大,我在最开始学喝茶、想用茶具的时候,大的碗配壶,两下就见底了,小的,我又觉得款式少,但是「不惑」的杯子体量我觉得用着最舒服。
裘航:其实我们也调整过两轮。最早我们做得杯型也很大,后来发现也存在你说的问题,一壶出来可能两杯半、三杯就没了,所以把它调小了。
汪浩:这也是个过程。设计之前也是有关注过“体量”这个问题,但是对“体量”的理解,就需要去和很多喝茶的人交流,他们是实实在在用过的。还有就是有些东西还有视觉体量和真实体量的区别,有些东西的视觉体量看起来大,但实际上它盛不了多少东西,这就需要在和你的设计主体之间互相转换:比如这个小杯子,是直口,但其实它有一定的量,它可能比某一些带盏的平碗的量还要大,所以这样的杯子喝茶就挺合适,所以,到目前为止这一年多的时间,在所有的地方给到的反馈,这一款是销售得最好的,简单、好用。



朱晗: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喜欢的或者对自己影响很大的设计师?
汪浩:每个阶段喜欢的都有。读书时,很喜欢一些家具设计师,比如瓦格纳,非常经典,倒不是说他设计的东西有多好看,而是说一个西方人的设计中融入了我们东方的元素,并且直到现在依然经久不衰,可能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但他的东西还是能告诉人们什么是经典:一件设计,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不落伍,有可能真的就变成经典了。所以说我们做茶器,或者看以前时代的人做得东西,到今天依然觉得它那么好看,包括现在还去复刻这些经典,那是因为没有新的东西能够去取代它。之后,等我自己出来做设计,就开始慢慢去关注和理解一些日本的设计理念。这个时候,可能就不是某个设计师或者艺术家的设计风格对我产生的影响了,现在要考虑的是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去设计,你的出发点和本质怎么再通过产品表现出来,而不是说我要做一个多漂亮的东西给别人看到,需要别人认可。
古奇:提到经典,你觉得我们所说的第一手段的复制,还有“山寨”会不会影响经典的设计?
汪浩:第一手段的复制,如果是在做合理的商业模式,我觉得我是认可的。一件东西之所以没有被淘汰,留存下来变成了经典,是因为这个东西是好的,如果对于这种东西人们不去把它延续下来,其实蛮可惜的。包括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北欧的设计师的设计,在大的型上对经典做一定的提炼和小小的改动,我觉得挺好。但“山寨”完全是另外一种概念,市场今年流行什么,什么东西火了,就用各种手段去做。复刻不等于劣质,“山寨”可能就是完全为了商业目的,以最低的成本换取最高的收益。
古奇:我这几年也在反思一个问题,刚出道的时候,我可能期望得到一件经典设计,比如瓦格纳的Y椅,但是几年后,到处都是这种椅子,我的感觉会受到影响,不想再去买这个椅子,我记得以前开咖啡馆时,非常喜欢潘顿椅,但是现在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汪浩:你去房地产交易会看,全是这个椅子,各种各样的颜色,哈哈。但我认为,以后并不是所有的产品都能被“山寨”的。我们所有的材质都是自己去挑,泥土的配比有自己的定量,和用料市场的现成的材料不一样,「不惑」的东西都是从源头开始到最后开发出来,我们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古奇:前两天我买了个铜壶,我觉得这个壶的质感很好,非常喜欢,拿回家给我老丈人看,老丈人玩古董茶器很多年,他说这个铜壶虽然工艺不错,却是假的、仿旧的壶。所以,为什么他们要去做仿旧这件事,是因为市场认这个旧、认这个款,做得人自己创新了,别人反而不买了,就像iPhone一样,每推出一款产品前,国外网站上会出来很多不同的设计,猜测iPhone是不是就长这个样子,但是一些山寨的厂商为什么不去用这些已经画好的图去做手机,为什么还要去抄iPhone?就是因为抄别的可能没有市场,消费者只认iPhone,市场决定了山寨的方向。
裘航:我们也一直在讨论,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有能力的人去做 “山寨”,做假,做旧的东西然后当假古董去卖,其实他们有这个手艺和能力创立一个新品牌,或者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这个完全可以自己实现。我觉得你说的这些山寨者,很多时候是受到时代大环境的影响,过多顾及眼前利益。但我们也欣喜的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慢下来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朱晗:最近在做哪些设计?
汪浩:就是现在楼下的三件新品,乌金的材质,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的材质的获得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不断尝试后发现可能比原来预想的还要好,现在出来的产品,从我们个人的理解上以及工厂给我们的信息上,都认为到目前为止已经全方位超越以前的产品。这一系列形态上非常适合和别的产品混搭,自己本身也并不张扬,也不是一定要唱主角的设计,非常耐看。功能上看,出水感觉好,包括重量也相当轻便,我们也拿现在能找得到的好的东西,包括日本陶艺家做得东西反复比较,不一定是竞争,但还是那句话,别人好的地方你一定要去学。


朱晗:不做设计时,生活中还喜欢做什么?
汪浩:我觉得 “拾垃圾”肯定是大家都喜欢的,就是去山里捡点东西,去看看国内外和我们类似的工作室和商铺,包括去日本的乡下拜访手艺人和作者,虽然可能有的作者并不是做陶瓷的,但他们手作时的状态,那种精神,对我们是有很大影响和帮助的。还有就是去了解每个行业,补充专业上的知识。我们做「不惑」的初衷是想让大家真正能用起来。如果这个东西不能用,但还能在市场上流通,只能是古董或工艺品。这种情况下,市场是很容易被商业引导的,有些东西是不是该这么贵?贵的是什么理由?但是用心的东西去延续传统,只要大家能用起来,传统的东西就不会被丢掉,因为有用就有市场。


「不惑」微博:@China不惑
“元白”展厅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滨盛路之江公寓三号别墅
开放时间:10:00~17:00 每周四~周六
采访:古奇、老梅、朱晗
摄影:张媚、「不惑」
文字:朱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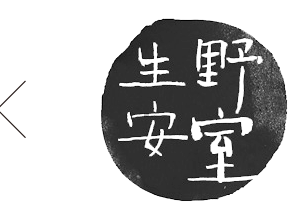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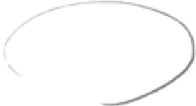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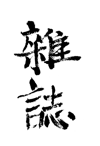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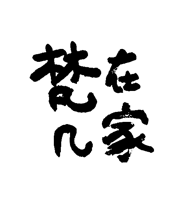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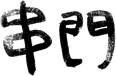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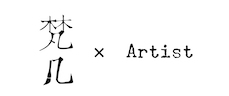

 客服部 service@fnji.com
客服部 service@fnj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