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就听说,深圳有一个玩木头的摄影师,叫强哥,能把一块平素的木头变成一件令人爱不释手的木作品。百闻不如一见,周末的早晨,穿过一大早就熙攘活跃的花贸市集,沿着主路走下去,便看见他在远远向我们挥手。
“哎呀,你们好!”他说,把我们领进他的工作室。落地玻璃门,厚重的木门把手,进了屋,是宽阔挑高的空间,几件胡桃木的中式家具,和从水里捞起来的巨大古木,湖水让它们形状各异,百态千姿,散发着时间的气息。这个大的空间为强哥和几个好朋友合用,他自己用两间,一间小的木工房用来创作,另一间用来展示自己的作品以及招待来访的朋友。





“彁”(gē)是强哥的手工木作品的品牌。木勺、砧板、托盘;黄杨、乌木、酸枝…强哥用不同的木头,依照自己的审美,做各种日常实用之物,线条流畅、优美,用料厚重,功力深厚。每一件作品都经历开料、敲凿、打磨、修改、上油等步骤。强哥说,自己是个木痴,一根海边拾得的木叉,他拿在手里看了看,做成一把勺子,但形状像魔杖一样狂野,仿佛威力四射。他喜欢做一些日常生活中用得到的东西,比如勺子,变化万千,或古怪、或童趣、或身段优美。虽然不像艺术品那样离生活有一定距离,但拿在手里,就感受到超越物体本身的魅力。强哥说:“我觉得很多东西都应该是为人服务的,是有人文关怀的,但它也不是超市里面卖的那种东西。机器永远取代不了人手,人手也代替不了机器,两者之间没有可比性。世界需要工业化,同样需要手工文化的传承。”






强哥美术学院毕业后,在深圳做了十几年商业摄影师,然后某一天,他厌倦了商业摄影的那些套路,决定逃离出来,一门心思开始钻研木头。也没有学过,拿起工具就着手开始创作,如同身体里某种机关被打开一般。黄强说,从木作的过程里,收获的是心的平静和满足。“自去年以来,我和别人说,我整个人就像电脑格式化了一样,重装了一个系统,”强哥说。“很多朋友不理解我现在在做的东西,说你摄影做得好好的,现在突然开始做勺子你这样行吗?(笑)其实怎么说呢,木头让我找回我自己。我的要求很简单,我觉得开心、按照自己的心意生活,想干嘛就干嘛,是最幸福的。”
梵几 x 彁



古奇:因为你的品牌叫“彁”,我很早关注你时和别人说起你,我就总觉得你叫强哥,结果今天见到居然被我蒙对了。
强哥:哈哈,对,我还去特地查了一下这个“彁”字,它确实没有什么意义,字面意思是指年轻的男子,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符号。我叫黄强,周围所有朋友都叫我强哥,包括比我年纪大的人,很奇怪。后来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说,我今天发现一个字——“彁”,你看这不就是强哥的缩写吗。我也没管对不对,反正就用它了。
古奇:我看到你做了很多勺子,每件都不一样,这些不同形态的作品都是怎么想到去做的?你做得过程中是拿着这块料想出来的,还是做一半想出来的?
强哥:其实我没有怎么想过,我会先拿着这块木头看,看到底做个什么东西出来。比如这是一个树叉,我就会保留它树叉的样子继续做下去。有时候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就拿斧头把木头削开,发现某个造型很好玩,然后去做一个东西出来,过程中会不断地修改。像这样的木皮,大部分人都会削掉,但我觉得留着也挺好玩的嘛。
朱晗:所以你是会根据这块木头本身的形状和特点去做不同的东西出来?
强哥:对,比如这种木头就是别人切完后剩下的那种废掉的,因为这部分有一个节在那里,很多人就会扔掉或者烧掉了,但是我把它捡回来,它本身就是一个切线,而我还要把这个切线放大。有些边角料扔掉了我觉得挺可惜的,有次我去福建仙游,看到那些木料就像山一样堆在那里,他们说六百块钱一车你拉吧,那些木头很漂亮,我就选了几麻袋寄回来。很多时候我买不了很多,我买那一点点木头人家都不卖给我。
我有一个“百勺计划”,就是希望做一百个勺子出来,然后可以一直展览。现在很多人问我,你的定位是什么?我真的也没有特别的定位,我觉得自己做得好玩,有生活的艺术,就是我的定位。它并不是普通的只能看不能用的东西,它可以放在那里观赏,也可以拿来用的,两者结合一下。





朱晗:怎么想到要做一百个勺子这个计划的?
强哥:最初我也是无意识的,后来做了很多勺子后,有一天摆在一起看,发现特别震撼,如果有足够大的桌子,把这一百个勺子一个一个地摆上去,真的很漂亮。其实这个计划的作品不单单只是这些勺子,做这件事的过程本身就像一次行为艺术。可能把这一百个勺子做完之后,我会做一百个盘子,也是有可能。
古奇:现在有多少把勺子了?
强哥:有六十多把,我其实一直都在做,可能已经有两三百把了,越做越觉得以前有些就不好看了,然后我又不喜欢,哈哈。其实如果说数量上一百个勺子是早就做完了。
古奇:我觉得你的勺子,很多都是无法复制的。别人拿到它,也不会真的去使用,去盛一碗汤或是怎样,因为这个东西的价值感并不只是一把勺子。
强哥:以前我也做了一些很好玩的偏艺术的东西,但那种东西跟我们的生活可能离得有点距离,我觉得很多东西都应该是为人服务的,是有人文关怀的,而且它又不是生活上面像超市里面买的那种东西,定位和“点”很重要,就是你要打动人。
古奇:我也一直在收藏椅子,有很多人特别追名师、大家的椅子,但我收藏的椅子里,名师的只是一部分,另一部分是生活中的、老百姓用的椅子。所以我想以后要不要也来一个“百椅计划”(笑)。
强哥:对,我这里就有这种民间的椅子,很便宜收回来的旧椅子,我看着很喜欢,这些就是民间的智慧,它们很朴素,但是又很实用,是为人服务的,这样的东西很令人感动。



古奇:我最开始看到你做的勺子,觉得出手很高,甚至在国外我也没怎么见过,跟我们这一代的相对年轻一点的手作人不太一样的。我们很多人都是模仿西方再结合自身的感受,一点一点去做,我并不是说这样不好或者不可以,但你是经过沉淀后,有一天突然开始做这个事儿,一个人的沉淀结合到自己的作品里,厚度是不一样的。
强哥:我以前完全没有玩过木头,突然有一天,我就开始玩木头了。真的是天生的,也没有学过,我就喜欢,就会去研究。我在instangram上认识了丹麦的一个做勺子的人,他每天也做很多勺子,他说他做的其实是比较特定的样子,反而觉得我做的比他好。
古奇:我觉得做木器不是特别难的事儿,但它需要无限重复加上个人领悟。
强哥:还有美感。我在装修自己工作室的时候,就请来一位木工,他看到我的这些东西就傻了,他说,怎么你会这样做这些东西呢?你是有学过木工吗? 我说没有。他很坚持,说这些东西是不能这样做的,我说,我就是想这样做(笑)。
朱晗:在做一件作品的时候你的整个状态是放空的,还是会思考很多事情呢?
强哥:如果脑子里要想事情,这样的话就没法去做了。我为什么不做摄影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你知道自去年以来,我和别人说,我整个人就像电脑格式化了一样,重装了一个系统。很多朋友不理解我现在在做的东西,有个高中同学甚至说我疯了,包括我姐也是说,你摄影做得好好的,赚钱的速度是一百二十分之一秒的速度,你现在做勺子你这样行吗?(笑)其实怎么说呢,我对自己的要求很简单的,不是虚伪,我觉得钱真的不是那么重要。我觉得开心、按照自己的心意生活,想干嘛就干嘛,是最幸福的。






古奇:你以前做摄影师,现在玩木头,都很成功,在这两者之间追求自我实现,你觉得这样两个角色哪一个更让你感到愉快?
强哥:玩木头。
古奇:做摄影是不是也经历了一个从愉快到不愉快的过程?
强哥:做一个自由摄影师,我觉得是很幸福的,但最终还是要走商业的道路,要为别人拍照,从见客户到做脚本、谈价格,一再修改,这样的一个过程真的很痛苦,最终出来的效果和我的想法几乎无关,我自己也不喜欢,这种东西已经不是我想要的。现在我玩木头,做任何一个东西都没有去考虑过这个东西要卖多少钱,谁会去买,我自己认为什么样子的东西做出来是好看的就会去做。做出来你想买就买,不想买就说明我的东西还打动不了你。
我现在做得这些事情很放松,什么都不想,就是在玩,就是喜欢,觉得很幸福,很快乐。人生很快就会没了,就是一口气,所以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的很多东西都是在老家那边做的,在那边有一个木工房,在那里生活的感觉很好,浇浇菜,吃简单的食物,番薯、粥,就感觉人生一下就很放松,很充实。做了一车东西,然后拉过来放在工作室,太有成就感了。以后我会把木头开好拿过来,然后在这里做一些细的东西,因为这里的灰尘和噪音都不能太大嘛。我这里的东西可以也可以让一些喜欢木头的朋友来体验一下。




采访:古奇、朱晗
摄影:达达、黄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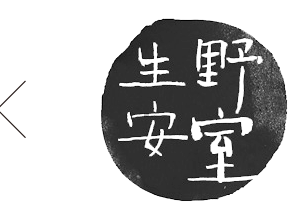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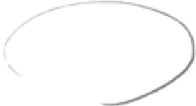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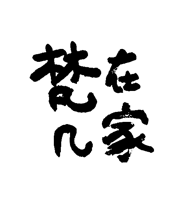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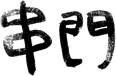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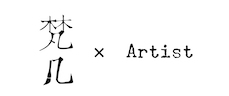

 客服部 service@fnji.com
客服部 service@fnj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