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译毅 一 一
「生活」藉由器物的使用进行着,而「器物」的质地,潜移默化影响着使用者的官能感知;「感官」建构出每个不一样的生活,而我们统称这项对于事物感觉的敏锐度为──品味。品味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改变,或可说,品味如镜,照映着当时的社会轮廓,即:一个时代的艺术与它的社会制度之间牢不可破的統一关系。
梵:
你的作品中有很多建筑材料的尝试,想知道一开始是怎么离开传统的艺术形式而采取更多的材料尝试呢?
彭:
因为我太太是从事建筑设计与建造的工作,所以我有机会接触到建筑材料与工法,而当时正好也对传统的艺术形式产生怀疑,所以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往未知的领域迈进,没想到过程中产生极大的热情,因此就持续到现在。
梵:
你的作品很抽象,泥土、铸铁也打破了原有的形态,赋予了更独特的美感。在抽象的背后是什么样的情感依托呢?
彭:
「传统」是厚重的,所以我的首要任务是让他看起来轻盈,因为现今生活过于沉重,我必须以「轻」的方式去面对它。我的作品作为鼓舞人们生活的物件,就必须要让人感觉到轻巧与流畅,这是我最初的思考。
梵:
你的作品里有泥土、石、铸铁、玻璃,甚至火焰也作为元素进入到创作中。有没有哪种材料或者工艺是非常得心应手?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两样。
彭:
夯土,农业时代常见的一种工法,在东西方皆可发现,据文献纪载,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农村就已经开始用夯土盖房子、炉灶或围塑火盆。可以这么说,每一块土壤皆可以拿来制作夯土器物,但得先经过土质分析才能得知砂与黏土的含量,并调整配比。首先准备一个有盖子的透明玻璃罐,将已干硬的土块捣成粉末状倒入罐中,加入水,转上盖,接着用力摇晃;砂较重,所以会先沉淀,如此一来就可以得知是否需要调整配比,一般来说,砂与土的比例约是3:1。当然,这只是一个参考数据,经验才是关键,各位不妨也可以挖起自家附近的土,做一个测验,说不定你也可以为自己制作一个夯土器物。

梵:
你的作品色彩偏于暗色系,是因为一些建筑材料的[因材制宜]还是你对这种颜色的探索或是独特喜爱?
彭:
以夯土为例,黏土是制作夯土的重要材质之一,而黏土的颜色会因地区而有所不同,例如红、黄、黑、绿甚至粉红色等。我倾向让土壤呈现他自己的本色,好似我与土壤的一种缘份,而缘分意味着不刻意产生,这点非常迷人。
梵:
人们在欣赏抽象的作品时会有一种心理:这不就是一块铁?这不就是砌墙的砖而已?等等这样的疑问属于一种大众心理。能在『欣赏艺术』这件事上分享一些心得体会吗?
彭:
社会进入现代化,快速、忙碌、流行、包装、视觉、八卦、消费..........,我当然不预期大众能有时间与心情去了解一件艺术品。 「艺术」是一种语言,就如同学英语,假如你不投入长时间,那么当然你也就无法看懂或听懂,特别在现今「诱惑」事物如此多的时代。不过我认为艺术家本身也有责任,这表示你和大众脱离太远,不过我倒不是要艺术家拥抱大众,因为这样的作品必然俗气,而是应该想个方法让艺术能间接的影响大众,所以我的方式是让作品能被使用,毕竟「生活」藉由器物的使用进行,而「器物」的质地更会潜移默化影响着使用者的官能感知;「感官」建构出每个不一样的生活,而我们统称这项对于事物感知的敏锐度为──品味。期盼通过使用、触碰,产生不同以往的生活经验。
梵:
你的作品通常会在美术馆或画廊的空间展出,这一次来到梵几,是不同于以往的空间,欣赏的人群也会更大众化,会对这样的形式有什么特殊的期待吗?
彭:
每个空间都有它的个性,而此性格皆会影响一个人当下的行为,例如我们到了图书馆,说话的音量自然就会压下来。梵几空间已形塑出自己的个性,相信前来的大众皆会在此氛围下调整自己的行为,我很幸运,梵几已为展览打好了基础。
梵:
之前有来过北京吗?这次来北京的感受是什么呢?
彭:
上次来是2007年的时候,记得当时还只有两条地铁,这次来已经十几二十条,车也多了,当然空气也有点不好受,不过对我这位短暂停留的过客,每天都像第一天,逛着胡同,踩着大街,拜访一区又一区的艺术聚落,非常过瘾。经验不同的生活环境对艺术创作者是重要的,所以我很享受在这里的每一天。
梵:
你平时会收藏一些艺术品吗?谈谈关于艺术品的收藏的一些体会吧。
彭:
艺术收藏毕竟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它考验着你我的经济能力,所以我只能分享个人对于收藏与自我文化养成的浅薄看法。
书,是一个最便宜的收藏,所以谈文化(文创)或从事文化(文创),如果家中连一本像样的书都没有,那还谈什么文化呢?
音乐,这也是最便宜的收藏之一,如果家中没有几首像样的音乐,永远打开电视作为居家生活的背景音乐,那还谈什么文化呢?
光源,更是便宜的收藏,中国古代谈明厅暗房,四字道出居家空间中,场域的转换与身体作息的相互关系,如果对居家的光源照明也没有感觉,那还谈什么文化呢?
最后,如果有点钱,买几件好作品,不只为自己,也为你的下一代留点好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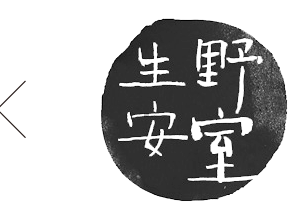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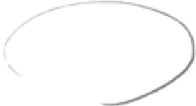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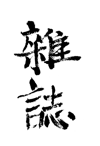






 客服部 service@fnji.com
客服部 service@fnji.com